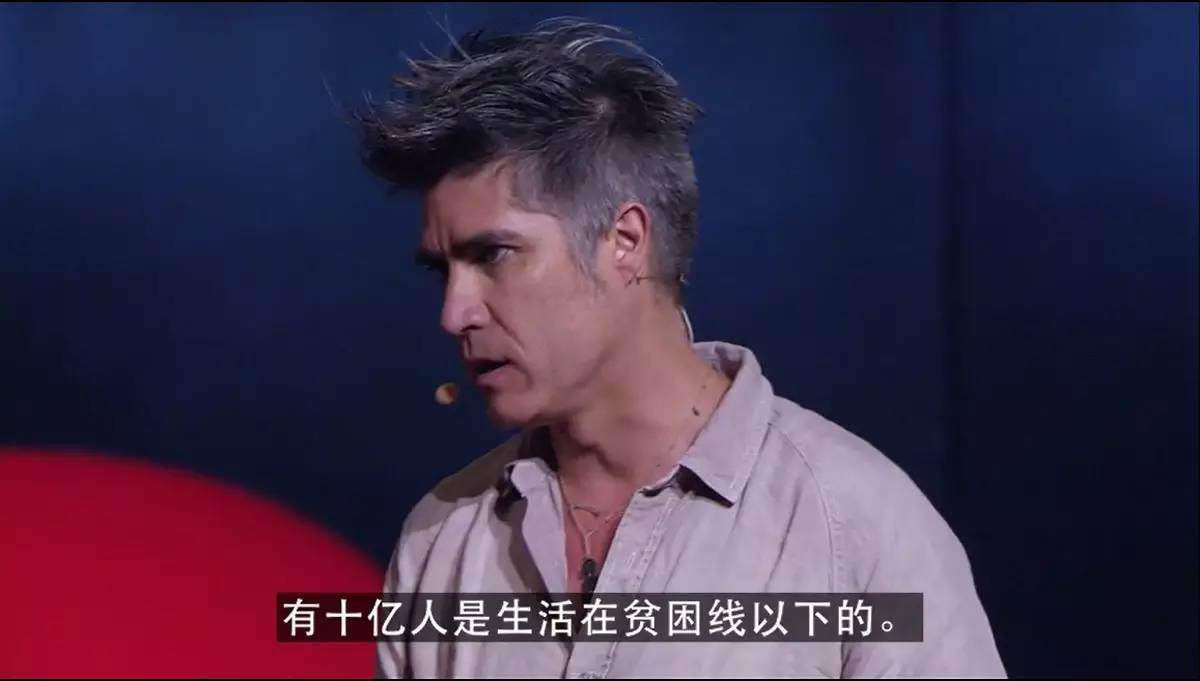Alejandro Aravena:为低收入人群设计最“恰当”的房子
来源:网友芝加哥公牛投稿 2016-0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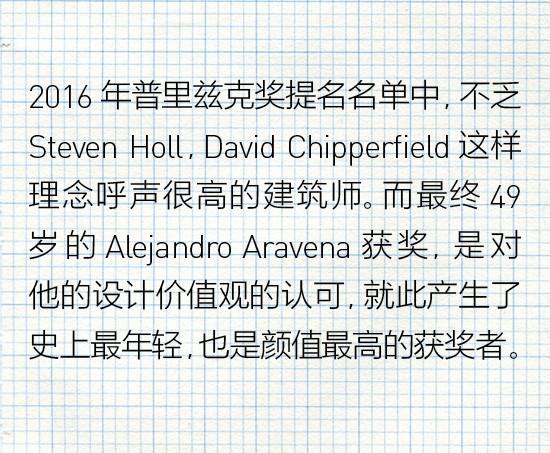
早在2012年王澍获得建筑界最高奖项普里兹克时,Alejandro Aravena与张永和同是评审团成员之一,他还就此非常认真的写了一篇关于这位在他眼里同样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建筑师的文章,在他看来,“王澍的建筑既不是怀旧也不是浪漫,而是因为务实和敏感,进而产生了一个恰当的结果。”
而“恰当”二字是他理解的设计三原则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deal with scarcity”和“irreducible”),就如同这把他为Vitra设计的“chairless”。
Alejandro Aravena第一次出现在上海公共演讲台上的时候,手里就拿着这样一把“椅子”,他的演讲获得了观众发自内心的喝彩和掌声。以下是记者在演讲会之后对他进行的一次长访谈,他不仅“恰当”的表达了自己的建筑设计立场和理念,还大胆的批评了一些在他看来无法苟同的明星建筑师。戏剧性的结果是,他如今也无可选择的成了一名头顶普里兹克光环的建筑师。他还是201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策划总监,拭目以待。
2007年的这次采访,我们在Aravena下榻的上海国际饭店的底楼碰头,当他得知酒店大堂的座椅是需要最低消费的时候,他拒绝了。这次长谈是在酒店大堂经理的办公桌上完成的。然而就在采访前不久,Aravena刚刚拒绝了哈佛大学的教席邀请,他选择了留在智利,以设计为工具,为低收入人群设计最“恰当”的房子。
AA= Alejandro Aravena
Q:做为建筑师,您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AA:当今建筑师的问题在于,他们所在乎的核心内容是“建筑师的兴趣”而不是“社会”。建筑师只愿意和建筑师对话,而没有触及社会的其它层面。
当建筑师开始关心社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不在乎做一些“差建筑”,甚至不把自己当成建筑师。举个例子来说,我所在的国家智利,主要社会问题是贫穷、发展、安全。媒体上所评论的所谓建筑的“风格”、“空间”等等,那些都是编辑记者们的谈资,没有人在意什么“风格”问题。就像窗外对面那个楼顶,如果换一个形状,不会有任何影响。
我真正关心的是,用建筑设计的工具,解决非建筑的问题。我企图想要解决的问题应该能够让每个人受益,就连那些走在大街上的人都能受益。用设计作为工具,用来解决设计以外的事情,因为“设计”在设计之外会更有力量。在我看来,建筑设计类的文章应该登在《时代周刊》或者《金融时报》上。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批设计师、艺术家都非常关注社会的贫穷、发展、经济等问题,之后他们中有的成了政治家,有的成为国际组织的领导人,结果就是他们不再做设计,不再做艺术。而今天的挑战在于如何既能够致力于社会核心问题,而不需要辞退设计师的工作。这也是当今设计师没有做的事情。
Siamese Towers 是Aravena为自己任教的智利天主大学设计的计算机中心,photo by Cristobal Palma
Q:对,建筑师无疑是所有设计师当中最接近权利和资本的群体。
AA:的确我们应该与政府对话,但是我更加愿意继续做建筑师。我们需要权利的力量完成一件事并形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我的角色是解决“怎样做(How)”的问题。人们通常更容易指出“做什么(What to do)”,而很少有人知道“怎样做”。
“怎样做”,解决的是“形式(Form)”的问题。但“形式”并非是指外观和造型。“形式”,在我看来,是指在空间范围内有策略的组织,可以是材料的选择,也可以是空间的序列,也可以是指人与人的关系。我完全同意建筑师应该靠近资本、靠近权利,但是一定会遵守我所说的这个“形式”的逻辑。
政治家、经济家不能解决“形式”的问题,但是工程师来了之后,经过测量评估可以给出一个基本模式。政治家会确定说“要怎样”,经济学家会说“是的,我们努力把它变成现实”,但是怎样做呢?什么在这里?什么在那里?这是建筑师解决的问题。
Siamese Towers, photo by Cristobal Palma
Q:奥斯卡·尼·迈耶是一个与政治结合紧密的建筑师,他也是当今中国某些建筑师的偶像。
AA:对于尼·迈耶的建筑和雕塑,我想说的是,你喜欢看女人,没问题,那是你私人的事情,我不感兴趣。但是尼·迈耶玩了很多这样的东西,他从别人并不知晓的地方得来灵感。他是巴西共产党,有足够的权利来获得建筑项目的委托。
但是我不认为尼·迈耶的建筑对于巴西来说有什么好处,而且他做的是“纪念碑”式的建筑。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巴西需要标志性的建筑,而尼·迈耶所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这期间产生的。设计从结构上讲不怎么样,但是外观看上去很有力量。但是我认为,仅仅是“标志”的话,那些建筑太昂贵了,他所做的都是纪念碑式的建筑,而从不关心“社会核心问题”。
如果真的是想做一个纪念碑,那么设计上可以相当自由,没有人会置疑“这个比那个更有标志性”。如果评判尺度在于“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的话,那么尼·迈耶就麻烦了。
Q:所以你更加强调建筑的功能性?
AA:我们通常所说的建筑的功能(Function)所指的范围太窄。建筑的形成受诸多元素制约,例如功能、预算、结构、使用、标识性和环境等等。我认为建筑师应该能够把所有这些因素清楚的展现并解决。没有哪个建筑能够声称是一件“艺术品”,如果是个“艺术品”或者“纪念碑”,那么不要来问我的意见。建筑不是什么很“高”的东西,相反建筑是很“低”的,应该能够和现实世界的所有事物交织在一起。而“功能”只是一个因素,重要的是应该和所有的一切相关。
Siamese Towers, photo by Cristobal Palma
Q:你如何看待那些明星建筑师的作品?
AA:弗兰克·盖里、扎哈·哈迪德等现在很多建筑师,他们在切断建筑与现实的关系,因为他们是天才。“我很优秀,这个项目给我做吧,不要问为什么,因为我是那么的优秀,你会喜欢我的设计的。”所以他们的设计也好,所做的一切也罢,都是在制造一个壳,把建筑包起来,把自己包起来。
他们当然有表达自己的优先权,他们也有自己的职业计划,共同点在于这些设计的出发点都是“个人的”、“内在的”,而恰恰相反,我认为设计的出发点应该是从“外部”开始的。首先我要了解的是有多少个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我从来不“发明”问题。首先我会聆听问题,之后再拿出我的看法。“使用和功能”的目的在于建筑之外,如果仅仅强调使用和功能容易让人误解。
Aravena为智利低收入人群设计的社会住宅, copy right ELEMENTAL
Q:但是,你不能否认盖里的古根海姆博物馆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
AA:二十世纪以来,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准则:给我自由,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建筑师被给予了这样的权利,“看在艺术的面子上,让我来做艺术的建筑吧。”结果就是建筑变成了不相关的事。
当建筑师发现他们的设计开始变得“不相关”的时候,他们找到了一种“相关”的方式,那就是让人们觉得“震惊(shock)”,人们被震惊了,这样就“相关”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明星建筑师喜欢做那些“震惊”的作品。就像是如果你没有糖,你会找一个接近糖的东西来替代。像扎哈、MVRDV、弗兰克·盖里,他们的手段就是“让人们感到震惊”,因为他们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不相关”的。
看看二十世纪那些伟大的建筑师,密斯·凡德罗,柯布西耶,他们的设计是在重建二战后的欧洲,关注的是社会住宅。而今天那些建筑师名人都在作什么?今天的逻辑是:想成功吗,那么就去设计博物馆或者文化中心吧!没有人关心那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问题,例如贫穷、居住等问题。高速公路对于城市的作用很大,但是有谁知道高速公路的作者呢?
建筑设计领域是最后一块“不同意见”不重要的领域。如果你和弗兰克·盖里说:“麻烦你把这条曲线稍微的改一点点弧度好么?”他会说:“不,在这方面,我是天才,我不在乎别人的意见,我要控制整个项目的全部。”如果你生病了,你会告诉医生是这里痛或者那里痛,但是你不能告诉医生手术怎么做,这是医生的专业。但是问题是,医生不会知道你哪里痛。而建筑师提供的就是专业服务,总有那么几个部分不归建筑师管。我开始学习放松,放松企图控制一切的企图。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设计留出了未来房主加盖的可能性。copy right ELEMENTAL
Q:怎样放松?
AA:在学校的教育里,我们没有学习过如何控制建筑师权利的尺度,建筑师通常认为自己就是这个项目的“所有者”,强调自己的“类型”,站在自己的星球上。于是进入社会之后,我们开始在自己周围编织了一个壳,把业主等挡在壳的外面。这样他们就听不到业主的需求,就是不知道病人哪里痛,怎么医治呢?这才是真正的失去了全盘的控制。做为建筑师,这样的结局就是,要么你是大师,像盖里那样,要么你什么都不是。
我在哈佛的时候,碰巧没有太多机会与建筑师相处,反而结识了很多工程师,我逐渐认识到工程师与建筑师介入一个项目的角度是那么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大型建筑师事务所的老板都是工程师而不是建筑师。因为建筑师的出发点总是“自身”。
Q:如果委托你博物馆的项目,你会怎么做?
AA:首先,我会尽所能的收纳来自这个项目之外的声音,我的习惯是尽可能的晚一些“喜欢”一件事情,我的习惯是先掌握相关的“问题”,花大量时间设置问题,之后再去解决问题。对于社会住宅这样的项目,涉及到了政策、资金、社会等问题,而建筑师的职责只是解决所有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建筑师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把项目外围所有问题进行组织排序,进而解决。而对于博物馆这样的项目来说,我也会采用传统的方式解决,就像我之前做的“暹罗塔楼”的项目,也是被要求做一个地标式的建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会用这种方式对待所有的项目。
智利天主大学UC创新中心 photo by Cristobal Palma
Q:这是你第一次到上海,亲眼所见的这个城市与你之前对上海的印象和想象,有什么不同?
AA:在来这里之前,我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具体认识。有一句谚语说,在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就是用你自己的“眼睛”看世界(look with our own eyes),而通常情况下,人们都是用“意识看世界”(look with our own minds),我们看到的是我们预期或者希望看到的东西。
事实上,我非常抵触在来上海之前抱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那么我到这里来就只是证实我之前的预期和想像。我只是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眼睛看上海。其实这个很难做到,听上去更像是某种呆板的原则,但是我的确是带着一双“干净的眼睛(naked eyes)”到了上海。
Q:那么在上海你看到了什么?
AA:第一件我看到的事情,当然不属于事实(facts)的部分。我看到的是“复杂的现状”,大量的能量,不停生产。就像这附近的那个工地,是一个“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的工地。第二件事,我看到的就是“特定规则”,人们似乎很有耐心。例如说在马路上的行人,有的人骑自行车、有人步行、开车的、乘公车的、打的的,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路径,这期间虽然产生竞争,但是每个人都能到达目的地。当某种命令发出的时候,例如红灯,每个人都能停下来,耐心的等待。要知道,“个人行为”与“公众原则”的结合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Q:在其它城市不也是这样的么,例如你工作过的纽约?
AA:在纽约,那是一个以“个人文化”为基础的地方,我不认为上海是这样的,在上海没有个人宣称“这是正确的”,但是在纽约,最正当的理由就是“因为我就是我,而我不属于任何团体。”
作家小屋,2015,瑞士蒙特里谢尔,photo by +2 Architects
Q:对于你来说,你来自智利,同时也在纽约和其它城市工作,你是怎样平衡不同城市之间的时间、经历和价值的分配的?
AA:这个问题,现在对我来说很清楚,我选择生活、工作都在智利。哈佛大学的任教工作结束后,我又收到了下一个十年的工作邀请,但是我拒绝了。
Q:为什么选择智利?
AA:首先,在智利,我做的事情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且与建筑之外的问题是相关的,例如ELEMENTAL的社会住宅项目。我可以为这些事情出力,并且有机会影响在建筑设计之外的事情。而不是仅仅考虑“这个线条是直一点还是弯一点”。另外一个原因是,智利足够的穷,你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必须接受所有的限制,通过创造力去解决问题。“规则越多,自由就越大”。当然我们也不是穷的什么都做不了,如果你有过多的资源,你什么都能做,那么你就无从选择。就会变得“武断、专横(Arbitrary)”,或者说“这样也行,那样也行(Otherwiseness)”。
我在哈佛做的第一个工作室取名为“Otherwiseness”,当今世界最糟糕的,也是最应该避免的就是“Otherwiseness”。你看窗外的那栋高楼,它的楼顶为什么是那样的形状?圆的不可以么,方的不可以么?这就是建筑师的随心所欲、武断和专横。“这样也行,那样也行”的结果就是“不管怎样都变得不重要了。”
诺华上海园区办公楼,2015在建,copy right ELEMENTAL
Q:智利能够提供给你这些“限制”,这是你想要的设计的前提?
AA:是的。在一个限制的环境内,你就可以避免这些“随意”和“那样也可以”(Arbitrary和Otherwiseness)。这样的条件迫使你的工作做的精确,而且必须尽快并且准确的针对问题做出回应。
最后一个原因是个人的原因,我对第一世界的问题不感兴趣。在美国和欧洲,他们正在遭受恐怖主义带来的痛苦,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因为他们对第三世界的态度和不同的文化都太过暴力、充满了野心,恐怖主义的痛苦正是他们在为自己的无知付出代价。而我个人,不希望在那样的环境下养育我的小孩。第一世界的问题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我不能让我的家人被动的去面对这些问题。
在智利,我们还能快乐的生活,可能不会太富有,但是会更幸福。我说不太清楚,简单来讲,在智利,我能吃到干净的水果蔬菜,甚至还能自己去河里抓鱼。最终是生命的感觉。也许我永远都不会,我也从不让自己加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建筑师”的竞争中。如果你加入这种竞争,你就必须选择纽约或者伦敦,代价就是“没有爱”。
Q:你现在不是正在着手准备纽约的展览么?
AA:哦,是的,但,这是一件好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说我对《Architecture Record》的评选不太在乎,我更加在意的是能够幸福的生活。
雷蒙特住宅,2015,墨西哥
Q:选择智利,可以做更多ELEMENTAL(基础的)的事情。
AA:是的,做社会住宅解决的是生存的问题。在ELEMENTAL,我们起先一年的时间都是在免费工作,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这个工作很重要。我们也会做一些有设计费的项目,但是我知道,这类的项目就没那么重要。后来智利石油公司看到了我们社会住宅的设计方案,他们就说:“你知道么,我们非常感兴趣,我们可以投资”。我没有个人网站,也很少参加鸡尾酒会,我也很少留下我的私人电话。有人说,这样你会错失很多机会。也许是,但是如果仅仅因为没有电话号码而丢掉机会的话,那么也不可惜。我不想把自己和业主的关系建立在类似电话号码这样“易碎”的基础上。这有一种过滤的功能,也是一个测试,留下的才是真正可以合作的业主。
Q:这也是一种策略?
AA:是的。毕业的时候,我的老师和同学都在关注,看我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设计,要知道我是那一界学生中各方面表现最出色的。但是在毕业后的第一个五年中,我什么都没做出来。而其它同学都做了各种各样的项目。他们看我的目光都是在说“哦,这个可怜的家伙,我都已经做了多少多少平方米的设计了”。而十年之后,他们还在做同样的事情,每天也在抱怨同样的事情。而我从一开始就在坚持,去做那些有创造力的设计,而不是按照别人的“风格”要求去交作业。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只有10个建成项目,但是每个项目都有分量,这不是数量的问题,而是强度和质量的问题。
Q:你知道中国建筑师的解决之道吗?他们一手做赚钱的项目,另一手做能够实现自己想法的项目,这样不是更加灵活?
AA:谈到钱的问题,我的做法是选择少的项目但是提高设计费,尤其是对于那些我不愿意接受的项目,我的要价会更高。例如有一对很富有的夫妇想为自己建一套别墅。你知道我不喜欢为私人业主设计这种豪华别墅,但是这对业主的要求很有趣,他们说“我们喜欢影子的颜色”,这也勾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就打电话问我的朋友标准设计费是多少,后来我的报价翻了个倍。需要的情况下,我也会“灵活”,只是我很少需要那种“灵活”。我学会了“对生活的要求很少(Live on litter)”,我花很少的钱,付很少的帐单,毕竟学校教师的工作可以为我解决基本的经济问题。
Alejandro Aravena为Vitra设计的“chairless”,是一条略带弹性的带子,使用者席地而坐。这样一件不能做任何“削减”的设计,是他一直以来推崇的建筑理念。
Q:在意大利威尼斯读书你都学到了什么?
AA:我发现很多所谓经典的书籍都在胡言乱语。在意大利的时候,我从不去上课,我每天都在城市街道上穿行,测量并欣赏我看到的建筑。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在整个意大利我做的就是这件事。罗马建筑有自己的一套体系,我不想在教科书上“读”这套体系,而是选择自己亲自实地考察的学习方法。应该说那段时间我在“吞食”自己逐渐形成的知识体系和原则,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我的习惯是先认清“骨架”和结构。另外我还学会了怎样测量一个建筑,学会了容忍误差,并且有意识的运用技巧引入“误差”做为解决问题的“余量”。如果不是这样的测量工作,我是不会发现帕农神庙前排柱子之间的差距。这也让我更加意识到,建筑师不可能控制所有的一切。通过测量,我还了解到,两千年前的罗马人的脚和现代人一样长,所以罗马时代舒服的楼梯在今天也一样是舒服的,但是我们依然被要求设计新的楼梯,所以建筑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只是解决方式不同而已。可以说,我的建筑设计原则是在意大利开始建立起来的,不过这也是偶然的机会使之所然。
Q:你是怎样教育你的学生的?
AA:我会要求学生写文本。维根斯坦说过:“世界被分成两个部分,一种是能被清楚的描述的事实,例如说树是绿色的;另一部分是不能被描述的。对于后者,我通常保持沉默。我不会用这样的描述方式:这“暗示”了、“意味”着等等。对于我,这部分内容要“沉默”。但这并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存在,它是存在的,只是属于“不去说”的部分。所以当我在谈论某个项目的时候,我不会说,“哦,我不喜欢这里”。我只谈论事实。面对这个世界,我用“做”来代替“说”,如果我要说,那么只说能说的部分,并且说清楚,就是谈论清晰的事实。相应的,能说的那一部分也是可控的。
我在接手一个项目的初始阶段,首先是用文字写清楚,之后再画草图。当然有的时候,草图在文本之前出现在脑海里,但是,我一直认为,只有当“写清楚”的时候,才能发现真正的创意。库哈斯是个真正的大师,因为他会“写文本”。
Alejandro Aravena
2016年普里兹克建筑奖获得者。1967年出生,25岁本科毕业于智利Católica大学建筑设计专业,之后一年的时间在意大利威尼斯学习建筑历史和理论。1994年开始独立建筑实践,并开始在智利Católica大学执教。2000~2005年为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在获得普里兹克这一建筑领域最高奖项之前,曾获得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特别奖,密斯.凡德罗建筑设计奖,2004年获得Architecture Record十大建筑先锋奖。
ELEMENTAL
2000年由Alejandro Aravena成立,是一间隶属于智利Católica Pontificia大学和智利石油公司,致力于着手参与如何解决全智利范围内贫困住宅问题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公司。
普利兹克奖
普利兹克奖是每年一次颁给建筑师个人的奖项,有“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1979年由普利兹克家族的杰伊·普利兹克和他的妻子辛蒂发起,凯悦基金会赞助。历年获奖的建筑师包括理查德.迈耶、弗兰克盖里、伊东丰雄、妹岛和世、王澍等,是全球建筑设计界最受瞩目的奖项,奖金10万美元,每年的颁奖活动也是业内的一桩盛事。
Alejandro Aravena普利兹克奖获奖感言
“回顾过去,我们深深感到庆幸。没有任何成就是归属个人的,建筑设计是一项集体协作的学科。因此,我们对所有为这些千差万别的力量赋予形式而做出贡献的人表示感谢。展望未来,我们预见到的是自由!这一奖项的声望、影响和庄严是如此崇高,我们希望以它为动力,探索新的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展开新的行动。登上这座高峰之后的路径尚待开拓。所以我们的计划是不制定具体计划,直面其中的不确定性,敞开心胸接受所有不期而至的东西。最后,着眼当下,我们感到喜不自胜,幸福满怀。这是欢庆的时刻,我们希望与尽可能多的人分享我们的喜悦。”
普利兹克奖评语
普利兹克先生表示:“评审团选出了一位令我们深刻理解什么是真正伟大的设计的建筑师。Alejandro Aravena首倡的协作方式设计创造了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建筑作品,同时也回应了21世纪的重要挑战。他的建造工程让弱势阶层获得了经济机会,缓和了自然灾害的恶劣影响,降低了能源消耗,并提供了令人舒适的公共空间。富于创新和感召力的他为我们示范了最好的建筑能够怎样改善人们的生活。”
发表评论
最新评论
 投稿
投稿